
2017年11月10日,以“东亚古代史研究的新展望”为主题的工作坊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挺阁召开。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副教授召集,邀请了十余位学术背景各异,但均关注东北亚地区历史的学者进行发表与评议。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余新忠教授、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孙卫国教授先后致辞,谈到本次会议采取小型工作坊的形式,且参会学者以青年同侪为主,可“在学术共通话题与共同追求下,开展更多的讨论与交流”。如所预期,此次工作坊对发表的五篇报告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简要摘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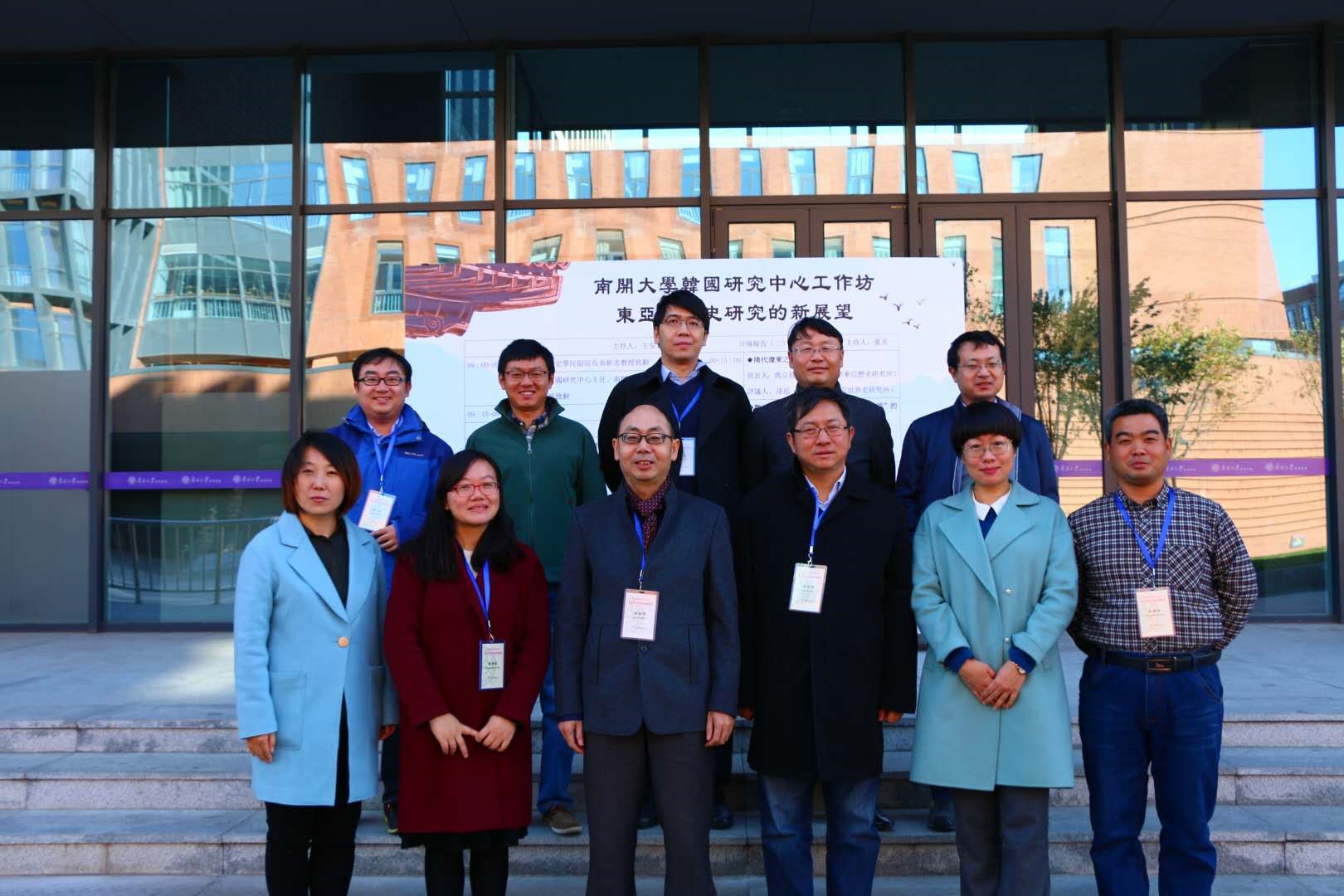
出土文献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
在会议的上午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飞峰助理研究员先后发表了《集安高句丽碑释读及相关研究》与《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考古调查和发掘收获》两篇报告。青石岭山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高句丽建筑址,目前已发现城墙、城门、蓄水池、金殿山遗址、大型建筑址、大量高句丽时期遗物及青铜印章等。在前一篇报告中,王飞峰先生则在整理中外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集安高句丽碑进行了重新释读与研究,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一,“国罡上太王”是好太王的王号而非谥号。二,“戊子定律”的“戊子”年可能是美川王29年。三,集安高句丽碑的年代大致在公元407年-412年。
对此,评议人长春师范大学郑春颖教授首先由考古学的眼光提出,光以肉眼释读碑文会丢失许多信息,若运用三维图像复原等新技术来研究,也许会有新的发现。然后举“国罡上/广开土境/永乐(平安)/好(圣)/太王”等其他称号为例,指出高句丽称号的结构有其独特之处,应反思是否可以套用中原的王号、谥号体系来看待高句丽的称号。“王号”问题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吉林大学赵俊杰副教授认为,“太王”、“好太王”、“好太圣王”这些称号与具体人物的比定应有所区分与斟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戴卫红副研究员亦提出,在东亚史研究中,存在以中原文物制度与外国联系比对的惯性思维。高句丽如何对待中原赐谥、是否存在其自己的名号制度,还可进一步研究。此外,学者们对烟户制度、“戊子定律”、生前抑或死后修陵等问题也所讨论。
王飞峰先生对出土碑石开展了细致的个案研究,戴卫红先生则对出土木简研究发表了高屋建瓴的报告——《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木简为中心》。戴卫红先生近年开始对韩国出土木简进行研究,其新著《韩国木简研究》已于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场报告中,她介绍了海内外的韩国木简研究现状、韩国木简出土情况、运用韩国木简可进行的具体研究、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并指出新罗木简、出土《论语》、日本木简等可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提出希望关注百济官制中自己的系统,强调了对其本国历史的研究。
对此,评议人赵俊杰先生主要从两方面提出了问题。其一是,在研究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播的某一分野——譬如简牍文化传播时,使用了大体相同的史料进行论述,若将简牍置换为其它,论证也同样成立。其二是,从考古的角度讲,还可以关注木简加工、缀合的方式与中国有何异同。南开大学夏炎教授由此引申,提到北大日前举行的“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研讨会上,关注历史材料“物质性”的讨论。王安泰先生则注意到韩国木简多基层文书,提出将高层人物与基层人物分开看待,考虑基层人物在接触中原王朝官制时如何理解、使用的问题。
基于传世文献之研究的新探索
在讨论集安高句丽碑时,孙卫国教授提出了“应如何合理解释留下的有限资料”的问题。这在东亚史研究,尤其是早期东亚史研究中,是始终横亘于学者们眼前的难题。为推进研究,在关注出土新材料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对传世文献做反思与再研究。在《制造“夷狄”:古代东亚世界渤海“首领”的历史话语及其实践》的报告中,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孙昊先生以渤海“首领”为切入点,对唐朝早期的朝贡记事、日本古代史乘附传、渤海遣日使团资料这三方文献进行了语境的重新考量,否定“首领”是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提出在当时东亚社会以唐朝为中心的封贡秩序语境中,诸历史主体并非被动接受“夷狄”定位,而是各自能动运用其政治话语,由此揭示作为边缘概念的“夷狄”是动态、相对的。
对此,评议人王安泰先生首先谈到了由“东亚”向“东部欧亚”的学术转变,强调“东亚”仍有其意义。然后将讨论带回“首领”一词本身,简单梳理了“首领”一词的起源及其意义变迁,并举出“左右大首领”、“界首子弟大首领”等例子,提出在一般意义上的随意称呼之外,应考虑是否还存在一种职官体系里的首领。
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黄修志先生《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一文,则旨于从东亚视野对“大礼议”之于朝鲜的影响展开研究。提出不简单从周边视角与异域之眼来看“大礼议”事件,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朝鲜的内外形势来阐释朝鲜的王权逻辑、政治构造、儒学观念、宗庙祭祀与对华关系。并指出在“大礼仪”发生的十六世纪,明朝儒学和朝鲜儒学之间开始出现思想上的分野,发生了“十六世纪的转变”。
对此,评议人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玄花博士后提出了一些补充,譬如朝鲜中宗即位两年后才得到明朝的册封,因此对明朝的政局变化会格外敏感;朝鲜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与现实和明朝有所不同,等等。孙卫国教授则在肯定此篇文章的研究意义后,指出本题还可进一步深入细致讨论。认为相较在学界得到更多讨论的“十七世纪的转变”,黄修志先生提出的“十六世纪的转变”只是一种“量的变化”,而未走向“质的改变”。
综合讨论:东亚史研究的再思考
在会议最后的综合讨论中,与会学者们就一天的研讨进行了讨论、总结与展望。孙卫国教授评论说,中国学者研究韩国史,常将之放在中国史的背景下考察,多关注中韩关系史;韩国学者则多在韩国史的背景下讨论,或有割裂中韩之间的历史联系者。王安泰先生亦谈到,希望大家加强对日本、韩国史本身发展脉络的关注,共同往此学术方向努力。戴卫红、孙昊先生提出,在目前的东亚史研究中,中日韩三国学界在使用一些学术语言时,有些各行其是,希望各国学者们能共同商议术语规范。在会议的最后,王安泰先生对诸位学者的参与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希望能将韩国研究中心这一工作坊的形式继续下去。
(供稿人:岳思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