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0日上午,在津南校区公共教学楼C319教室,本学期南开史学前沿系列讲座迎来了第一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晏绍祥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以“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及其政治作用”为题,为学院师生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此次讲座由历史学院副院长丁见民教授主持,俞金尧、张荣强、王美平、张叶、徐朗等老师以及学院全体硕博一年级学生共同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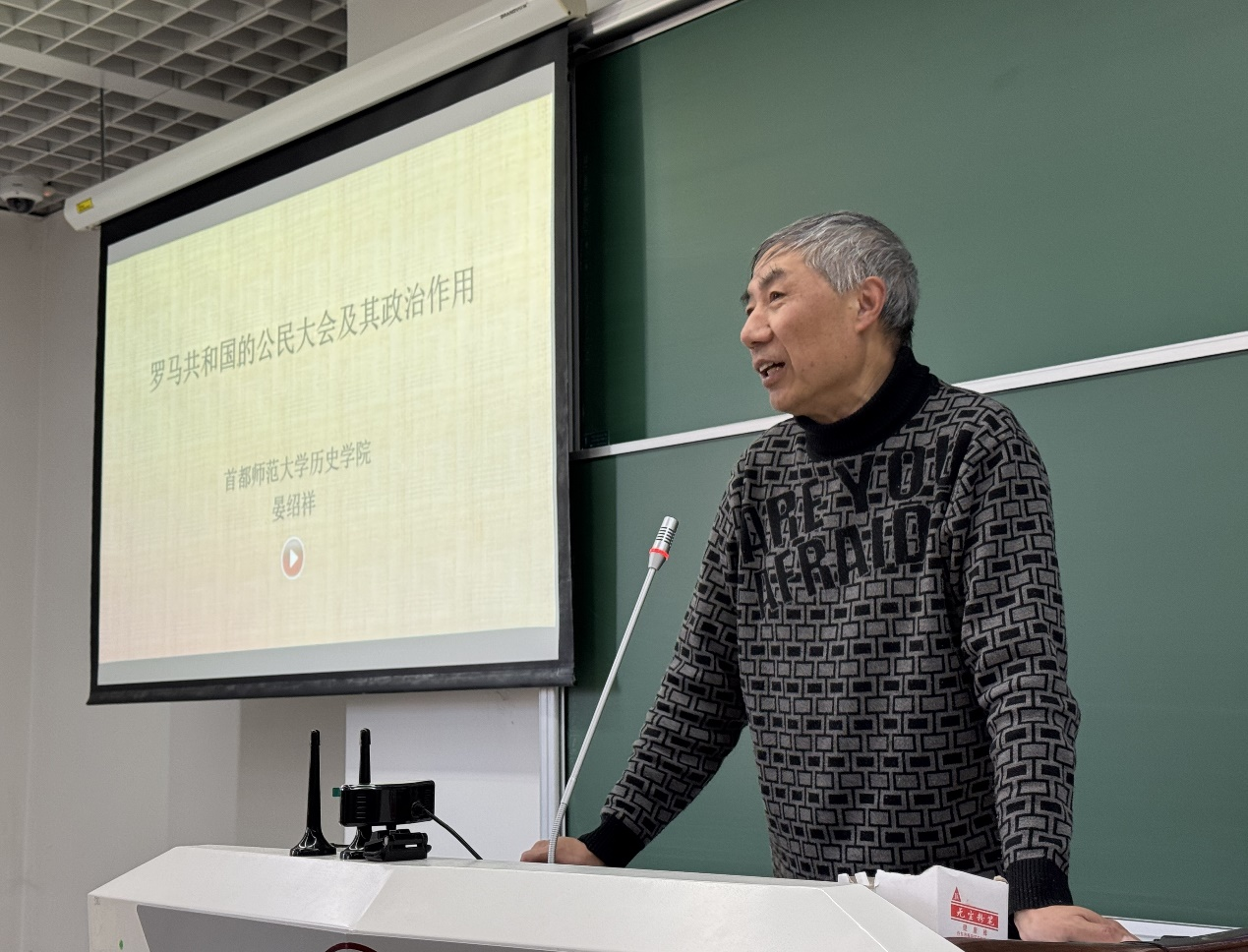
讲座伊始,晏教授以公元前287年《霍腾西阿法》的颁布及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改革为时间节点,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平民贵族斗争阶段、稳定发展阶段与内战阶段三个阶段。他进一步指出,罗马共和国的国家结构与古希腊城邦相似,均视公民为国家政治的核心主体。通过意大利同盟城市与山内高卢行省的实例,晏教授阐明,尽管这些地区处于罗马统治之下,却并未享有完整的罗马公民权,前者多以同盟者身份参与战争,后者则仅承担臣民的赋税义务。虽然罗马的公民范围随着对外扩张而有所拓宽,但是以公民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却始终如一。
在制度架构层面,晏教授深入剖析了罗马政治的“三驾马车”——高级官员、元老院与公民大会。他详细介绍了执政官、副执政与监察官的职权范围及历史地位,并强调了罗马官僚制度的义务属性,这使得平民难以参与政治而使高级官职多为富裕世家所把持,对罗马政治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元老院作为常设机构,其权力广泛,包括外交谈判、副执政权责划分、执政官卸任后行省安排、公民大会决议审批以及官员监督等,而元老的终身制更是确保了其政治影响力的延续。
随后,晏教授转向古典共和国时代的公民大会。在共和国时期,公民大会主要有库里亚大会、森都里亚大会、部落公民大会和部落平民大会四种形式,各有其独特的职能与运作方式。库里亚大会作为最古老的公民大会,主要负责新任执政官的仪式性授权;森都里亚大会相传为塞尔维乌斯改革所创,以财产为标准划分五个等级、193个百人队,以百人队为单位进行投票,但是富有的第一等级控制着一半以上的票数,决定了森都里亚大会的寡头性质;部落公民大会由高级官员主持,主要权力是立法和选举贵族市政官、财务官,以地区部落为单位,每个部落一票;部落平民大会则是由保民官主持,选举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官,具备通过立法并且弹劾官员的职能。因为罗马平民大会不允许贵族参与,且部落平民决议自公元前287年后开始对全体公民有效,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平民的利益。晏教授还介绍了预备会这一特殊的会议形式,通过在决议生效前提前实行公示,倾听舆论来参考民众的意见以促进法案的批准和实施,体现了公民大会的制度弹性。
晏教授也指出,罗马公民大会的民主参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限制。其一,公民大会的直接参与制导致边远地区小生产者政治参与成本过高,国家大权为贵族和精英人士所控制。其二,罗马公民没有自主集会的自由,主持人可以控制会议的进行。其三,保民官团体的矛盾与派系倾轧制约大会效能。其四,公民大会的议案必须经元老院的准可才能生效,在制度上限制了公民大会的作用。其五,阴谋活动和暴力行径也在破坏公民大会的正常秩序。正如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提出:官员是活的法律;史学家萨鲁斯特与李维也在著作中提供大量例证指出,执政官在某些家族中传递;史学家蒙森(Mommsen)认为,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农民共和国,贵族特征从未从该制度上消失。随着罗马的扩张和公民权的扩大,众多远离意大利中部的公民难以前往罗马城行使民主权利,罗马的公民大会会场也逐渐难以容纳数量庞大的公民群体等等因素都在限制着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因此,罗马城邦式的公民大会在运行中也逐渐走向寡头制,并最终解体。
最后,晏教授总结,在制度设计上,罗马共和国属于城邦制度,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大会拥有极大的法定权力,这使得罗马共和国符合民主制度的形式条件。但从实际运作角度看,罗马的社会结构、精英阶级的优势,以及共和国各种制度上的设计包括对公民大会的限制,使民主程序异化为寡头统治的工具。这种“民主外壳包裹寡头内核”的独特形态,既解释了波里比阿(Polybius)的混合政体理论,也呼应了芬利(M.I.Finley)关于古代民主局限性的经典论述。讲座结束后,晏绍祥教授同与会师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讲座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之中圆满落幕。
供稿:董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