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7日上午,本学期南开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在津南校区公共教学楼C319教室举行,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春声教授主讲,主题为“南岭山脉与客家族群——兼及王朝制度、知识建构与族群认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主持讲座,代表学院对陈老师莅临南开表示感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余新忠、孙卫国、张荣强、张传勇、贺江枫、张叶、史正玉、外国语学院李蕾和天津师范大学罗艳春、吴倩等校内外老师,以及历史学院硕、博一年级全体研究生共同参加讲座。

陈春声教授首先结合自身经历,总结近著《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一书的三条线索——人群、社会、信仰。随后,以“何谓客家”开篇,分11个部分讲述南岭民族走廊的地域社会历史以及客家族群认同的形成过程。他指出,传统上不以郡望或籍贯表达身份的人群,通常被视为“化外之民”,如“苗人”“猺人”“蜑民”等。而“客家人”的称谓则是一种特例,需要从地域(或籍贯)认同、方言群分类意识、近代族群观念等角度思考。
在分析南岭山脉与客家族群的地理分布时,陈老师指出,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区位于闽、粤、赣、湘数省交界,但与明代南赣巡抚辖区、中共中央苏区高度重合,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或可由此得到启发。陈老师又引述费孝通“南岭民族走廊”的观点,并钩沉大量历史文献,描绘“客家”之前的南岭。他认为,南岭山脉“猺”“獠”“畲”“蛮”等人群杂居,加上从周边地区不断流入的逃逋、脱籍之人,在地方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不时被称为“客輋”或“畲客”等等。而所谓“客家话”可被视为南岭山脉的“普通话”,即居住于此的各类人群都会讲的共同语言。明代中叶南岭山脉的“猺人”大量“汉化”,清初才有“客家”这一称谓出现。十六世纪南岭山脉东部地区山贼、盗乱频发,与“徭人”“疍民”等大量“汉化”的过程密切相关。明中叶以降,南岭地域军事性围寨的大规模兴建,改变了乡村的聚落形态。这是明清之际南岭山脉地方社会整体转型的组成部分,积淀为本地建筑和聚落具有某种“理想模式”的典型形态,影响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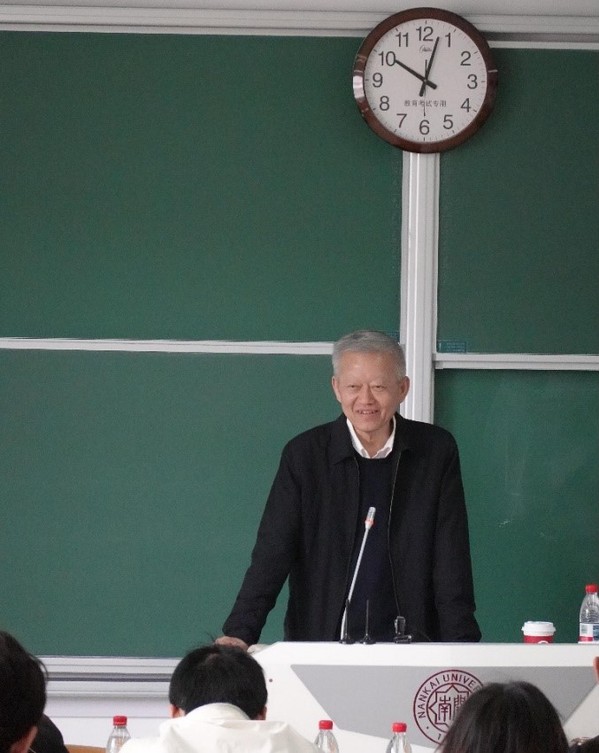
宗族记忆的背后是国家的历史。明代后期,华南地区出现明显的“宗法伦理庶民化”倾向,嘉靖以后,宗族意识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宗族礼仪在地方社会得到推广,可视为地方上的身份认同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过程。客家人通过所谓来自宁化石壁的祖源传说,构建起宗族来源的共同记忆。清初,“迁界”与“复界”的社会变动,使原本山居的讲客家话人群有机会顺势向外迁徙,移居粤闽沿海地区及广西、江西、四川、台湾等地,形成所谓“客家迁移运动的第四时期”。清中叶以前推行的“粮户归宗”,是对康熙中期以后宗族组织日益发展、宗族在乡村地位日渐重要的社会现实的承认,反过来也鼓励了宗族组织的迅速发展,促成多姓村向单姓村的转变。陈老师强调,如今南岭山脉中乡村地区常见以宗祠为中心的“聚族而居”,存在很多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寨的建筑和社会景观,其实是在明清之际两百年间地方社会急剧动荡及一系列制度转变中形成的。
近代是客家族群意识形成的重要时期。其一,土客之争与客家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关联,如咸同时期的“土客大械斗”。其二,近代城市生活也推动了族群观念的强化。汕头开埠以后,大量客家商人、文人参与近代市政与城市文化建设,潮、客方言群体因接触而产生的认同或分类感觉日益明显。其三,现代知识传播也影响了客家身份的建构。罗香林所著《客家研究导论》促成了“客家”定义的标准化与“历史记忆”的重新创造,其提出的“民系”观念,亦推动了“福佬民系”与“广府民系”的建构。客家研究的学术史,也是“客家人”形象被不断塑造、身份被不断强化、超越传统地缘意识的认同感被有心无意地培育起来的过程。这是个人知识建构与群体意识塑造的典型案例。陈老师在结语中再次强调,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一种“解构”,一切理所当然的概念都应该追溯其形成过程,并对其进行有深度的、辩证的分析,在中国尤其要关注历史观念背后“无处不在”的国家意识形态。

讲座最后,常建华教授进行总结,他称赞陈老师既是解构故事的高手,也是讲故事的高手。陈春声教授的演讲启发性强,语言轻松诙谐,妙语连珠,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